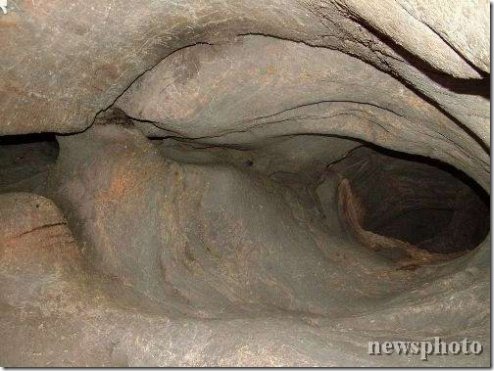以下正文:
就笔者所见,目前有关阴门阵的研究已有James Parsons、泽田瑞穗、相田洋、李建民、及Paul A. Cohen等人为文探讨,其中以李建民较为深入。本文即以这些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女体与战争的关系。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以女性裸体为主的阴门阵的内容及特色为何? (二)女性的身体为何具有厌炮的能力?(三)何种身分的女体具有厌炮的能力?总的来说,阴门阵提供了我们探讨明清的女体与战争关系一个相当好的例子。我们认为,日本学者泽田瑞穗与相田洋的「以阴克阳说」似乎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阴门阵现象。当我们把视野扩大至女体与厌胜关系时,义和团团民的心态反映了明清妇女裸身所具有的污秽象徵意义,而这套观念自明末以来被运用在战事上。义和团运动时,裸妇被视为是保护洋炮,破除法术的主角,这和明末清初以阴门阵抗炮所隐含的观念相类似,都认为女体??尤其是裸妇具有厌胜力量。义和团的这种视女体污秽的观念正可解释为何在明末以来的战争中,会出现用裸妇来厌炮的阴门阵现象。
关键词:女性 身体 战争 阴门阵 术数 巫术 火炮 妇女史 身体史
一、前言
(保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鲁迅)「那麼,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是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炙疮疤。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亦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1]
这是一段鲁迅小时候与其保姆阿长的对话,其中「长毛」泛指洪秀全的太平军及一般的土匪,文中描述清末太平天国之乱时,阿长被太平军叫去裸身站在城墙上抵御清军,原本鲁迅以为他保姆只有满肚子的烦人礼节,却不料她还有如此伟大的抗炮神力,从此以后对她产生特别的敬意。类似太平军这种以妇女裸身方式对抗大炮的方式,明末以来有其专门的称呼——「阴门阵」。有关阴门阵的记载,在目前有限的资料中,大致可上推至明末。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 H. van Gulik,1910-1967)曾於《中国古代房内考》提到此种现象:「十七世纪早期,残暴的军阀张献忠(1605-1647),作为当时为四川省的主要军事统治者,曾将被屠杀的裸体女尸暴露於被围攻的城外,想用它产生魔力,防止守城者的炮火」。他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转引美国研究明末反乱的学者James Parsons一九五九年的研究,[2]这种以妇女裸身方式抗炮的例子,在张献忠之后不仅有增多的趋势;而且对此现象的指涉更为明确,「厌炮」、「阴门阵」的名词屡见於后来的战事文献中。本文所谓的「厌炮」则指与火炮有关的厌胜法术「阴门阵」,它不仅可抗炮,亦可助炮。「厌」有镇压、镇服、压抑及禳除之意,意指以强力镇压、逼迫、排除某种东西,使之屈服而取胜。严格来说,所谓的「厌胜」之术,并非单指某中特定法术,而是泛指在手段及方式上带有强制性的法术。依林富士的看法,其施行的目标和目的可粗略分为疾病、水灾、火灾、生育、权位、战争及谋杀七种[3]。本文的阴门阵则属於战争类中的一项。
相较於中国,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亦有类似的例子,但内容与意涵皆与阴门阵不同。在一七九二年法国报纸的一幅漫画中,图中法国贵妇裸露下体及臀部,而雅各宾党(Jacobins)手执象徵男性性器官的腊肠与奥地利军队对峙,这幅漫画表达了男性对当时的政治及女性角色转变的焦虑与恐惧(见附图一)。Lynn Hunt的研究,有助於我们思考性别与政治或军事间的关系。[4]就笔者所见,目前有关阴门阵的研究已有James Parsons、泽田瑞穗、相田洋、李建民、及Paul A. Cohen等人做过探讨,但以李建民的〈「阴门阵」考——古代礼俗笔记之二〉较为深入。[5]本文即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女性、身体与战争的关系。[6]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以女性裸体为主的阴门阵的内容及特色为何? (二)女性的身体为何具有厌炮的能力?(三)何种身分的女体具有厌炮的能力?
二、 女体与火炮
(一)阴门阵的出现
女性自古以来在战事上即从未缺席,其职司从女将、女兵到军妻、军妇、营妓、军伶皆有。顾颉刚曾说:「古代平民女子亦能当兵,执干戈,且从事守城者倍多於丈夫也。」[7]这个说法近来已由大陆学者王子今的著作《中国女子从军史》得到印证。[8]但女子参与战事最特别地莫过於明末以来藉裸体妇女对抗火炮及法术的阴门阵。
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的阴门阵例子并非如日本学者相田洋所说,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杨应龙之乱;[9]而可再往上推至万历元年(1573)李锡平清州的瑶、僮、伶及侗族之乱,关於该战役,《明史》记有:「……贼奔大巢,亘数里,崖壁峭绝,为重栅拒官军,镖弩矢石雨下。妇人裸体扬箕,掷牛羊犬首为厌胜。」此段资料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西南少数民族妇女裸体拿著箕器是对抗官军的火炮,但从史料「李益徵浙东鸟铳手」看来,应有以厌胜之术来对抗火炮的可能性。[10]至於杨应龙之乱,辽东巡抚李化龙(1554-1611)於《平播全书》中提到:「酋用邪术,令妇人数百人排立高处,去衣执箕,向我兵扇簸,而贼锋甚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11]此处的「酋」,指的就是明末四川播州民变主脑杨应龙。[12]这两条资料提到几个现象,(一)阴门阵的阵法主体是裸身的妇女。(二)裸妇手拿箕器搧动,并丢掷牛羊狗的头来厌胜。(三)官方对阴门阵的回应则采取传统数术洒狗血方式。特殊之处是妇女裸身,并拿著「箕器」在扇动,这是在明以前的战史中从未有过的现象,在此之前的战史,顶多像元军猛攻朱元璋时,采用「遣妇女倚门戟手大骂」的心理镇吓方式而已。[13]针对反乱军所施行的阴门阵,李化龙所采取的做法是洒黑狗血的方式。关於这种做法,《平播全书》中「破贼厌镇法」有较详细的描述:
为军务事,据营中报,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炮不得中,此厌镇法也,合行破解,为此票仰分守川东道,即便移文监军二道知会,以后遇此令,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14]
这段引文更进一步提到了,反乱军所使用的阴门阵,主要对付的是官军的火炮,只要官军一用火炮,反乱军就立即令营中妇女脱去身上衣物,以箕扇之。反乱军以厌法对付官军枪炮,一个可能就是双方武器相差太过悬殊,从《平播全书》中我们可发现杨应龙阵营,并无任何火器。[15]官方对於此种阵法,只知是一种「厌镇法」,尚未明确地提出「阴门阵」的说法,可能此时「阴门阵」尚未普遍的缘故(表一,案例1)。
有关杨应龙反乱军使用阴门阵一事,方以智(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的《物理小识》亦提到:
李霖寰大司马征播,杨应龙败逃囤上,李公以大炮攻之,杨裸诸妇向炮,炮竟不然,此受厌法也。崇祯乙亥,流贼围桐城,城上架炮,贼亦逼人裸阴向城,时乃泼狗血、烧羊角烟以解之,炮竟发矣。故铸剑、铸钟、合至丹药,皆忌裙钗之厌。[16]
方以智在此很清楚地指出,火炮无法发射是受到妇女裸身的厌胜之法的影响,并类比至古时的铸剑、铸钟及制作丹药,都是严禁女性参与。到了崇祯年间,阴门阵的事例逐渐增多。这条资料另外所提的崇祯八年(1635)桐城之乱,指的是张献忠随著闯王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并进入安徽,克颖州,破凤阳等地一事。[17]面对张献忠军队的咒术,桐城官军不只采取类似对付杨应龙之乱时的泼狗血行动;亦透过烧羊角烟的方式来反制。
阴门阵除了以妇女裸身抗炮以外,有时亦会参杂其它厌胜法术於其中,例如崇祯二年的贵阳之乱,当时贵州巡抚李澐率守军抵御奢崇明等叛军的围攻,叛军以三丈楼临城,「用妇人、鸡犬厌胜术。澐、永安烹彘杂斗米饭投饲鸡犬,而张虎豹皮於城楼以祓之,乃得施炮石。」[18]以鸡犬厌胜方式来助攻,倒是首见。更特别的是,官军对於这种厌胜之术,则采以猪肉混合米饭投饲鸡犬及悬挂虎豹皮的法术方式来反制阴门阵。
崇祯九年(1636)的例子则对阴门阵的描述更加详细,崇祯九年正月,张献忠随高迎祥等再次下安徽,不久,张献忠则转战河南、湖广一带:[19]
崇祯九年丙子……癸丑初七,贼四卤村落,搜山谷,获妇女,裸而沓淫之,委顿,断其首。 刳孕妇腹,咸倒埋之,植跗露其私,环向堞数百躯。城上壮士回首不忍视。贼噪攻城,城上鸣炮,炮厌,皆裂,或暗不鸣。城中惶恐。觉斯立取民间圊牏数百,悬堞向外以厌之,炮皆发。贼大创,无所泄愤,围益急。[20]
此段所描写的就是张献忠攻打安徽滁州的残暴战况,和前面几则例子不同的是,这则资料透露了妇女在此次战役中,不仅裸身,而且被奸淫、杀害、断头,甚叛军将孕妇剖腹,倒埋入土中,只露出其阴部,这种乡民被迫害的惨状对城上官兵的心里震撼相当大,在此挟厌法及心理作用的战略攻击下,城上所发射的炮弹无一成功,或无法发射、或裂开,造成城内军民严重的恐慌。太仆卿李觉斯见此颓势,亦采取反制的做法,他的方式是收集民间所用的粪器,将其悬挂在城上矮墙上(表一,案例2)。为何便器会被视为可克阴门阵,下节有较详尽的讨论。
(二)阳门阵的反制
张献忠之乱时所采用的阴门阵可视为阴门阵的雏形,尽管他并非第一个使用阴门阵的叛军,但由於该次战役的震撼性,加上他在当时反贼中的声望,这种阴门阵的厌胜方术很快就传遍其它地区。之后,女体与战争的关系有日趋复杂的趋势,其中,阳门阵的出现即是最明显的例子。
目前所见最早出现「阴门阵」名称的例子是明末大将李光壂(1596-1662)的《守汴日志》,该书记有:「崇祯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贼用阴门阵,城上以阳门阵破之,多备锹橛,每日就贼掘处,城上分中掘透。贼趋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骂,城上点大炮,悉倒泄。城上令僧人裸立女墙叫骂,贼炮亦倒泄」。[21]崇祯十五年(1642)一事,指的是李自成三次率军围攻开封,李光壂当时身在开封,不仅目睹李自成等农民军围成的全部过程,而且与明朝开封守臣高名衡、黄澍一道,谋划守城防务。开封第二次被围时,他担任左所总社,第三次被围时,则负责义勇大社总巡事务,日夜随守臣巡城,崇祯十五年九月,黄河决口,开封淹没。李光壂可说是全程经历了开封被围的全部实况。这条例子不仅首次提到阴门阵,亦提到「阳门阵」这个名词,所谓阳门阵,在此使用的方式是叫僧人裸体站在城墙上对敌军叫骂,其效果如同阴门阵一样,可令火炮失效。僧人被视为具有反制阴门阵厌胜的能力,似乎有以阳克阴的对应关系(表一,案例3)。
此事在之后的清代笔记中亦有记载,可见在当时相当受到瞩目。例如《豫变纪略》记有:
崇正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怀庆地震,时贼围攻甚急,守亦甚严,虽张许之守雎阳不如也。炮石如雨,中则麋烂,贼患之,乃驱众妇人,裸而立於城下以厌之,谓之阴门阵,城上之炮皆倒,泄而不鸣,城中将吏乃急命诸军,裸立而燃炮,谓之阳门阵以破之。贼之炮石亦倒泄而不鸣,异哉!阵名自蚩尤、黄巢以来,攻战多矣,未尝闻此也。[22]
《三冈识略》对此事亦有详细的记载:
先是流寇围汴粱,城中固守,力攻三次俱不能克贼,计穷搜妇女数百,悉露下体,倒植於地,向城谩骂,号曰阴门阵,城上炮皆不燃,陈将军永福取亟取僧人,数略相当,令赤身立垛口,对之谓之阳门阵,贼炮亦退后不发,详见李光壂汴围日录中,后群盗屡用之,往往有验,尝考黄帝、风后以来,从无此法,惟孙子八阵中,有牝牡之说,此岂其遗意与?[23]
这些资料透露了几个讯息,第一、阴门、阳门阵后来亦被清代的盗匪所沿用,第二、明末之前的战役未曾见过有此阴门、阳门阵法。据董含的看法,这个阵法与孙子兵法中的牝牡之说类似。就在李自成於河南围攻开封的同时,张献忠则一直在安徽舒城、霍山、合肥一带进攻。清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对此记有:「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贼攻舒城。知县章可试塞三门,开西门,诱贼入,陷於坑,奔溃,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县裸妇数千,詈於城下,少愧沮即磔之。攻三日而去。嗟嗟!妇人何罪,裸之磔之,贼之凶恶,一至於此」。[24]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转而进攻四川,同年六月占领了重庆,亦使用了阴门阵:「贼围城之第一日,命一人至城下说降,城中守者不应,第三日,贼命两妇人裸体在城下秽骂,城上亦不解何故」。[25]
综合上述例子,我们会发现叫裸妇在城下辱骂官兵,似乎成了一定的模式。阴门阵除了在明代常被反乱军所用外,我们亦可发现官方袭用此阵法的例子,例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清水教之乱时,王伦军队围攻临清新城,城上清军所发铳炮皆无法击中王伦军队,遂叫妇人裸身,并配合洒鸡血的方式来厌胜,最后才击退敌军的火车攻势。[26]对於此事,清代档案亦明确记载了类似场面,乾隆皇帝还过问此事。大学士舒赫德在奏摺中有详细的记载:
临清西南二门俱有关圣帝君神像,纵有邪术不能胜任。然起初施放枪炮,则竟敢向前,叶信因想起俗言黑狗血可以破邪,又闻女人是阴人,亦可以破邪,是以用女人在垛口向他,复将黑狗血洒在城上。那日放枪即打著手执红旗的贼目,各兵踊跃放枪炮,打死贼匪甚多……。[27]
这条资料明显的提到,清军认为敌军在炮火的攻击下,竟然不畏火炮,继续向前,必定有邪术助仗,守军协副将叶信听闻黑狗血及女人可破邪,遂叫女人立於城墙上向著敌军,夹以黑狗血泼洒在城墙上,火炮效力才陆续发挥功能(表一,案例4)。对於此事余蛟的《临清寇略》有进一步的说明,他提到,当时有位身穿黄繗马挂,佯称王伦之弟的四王爷,右手执刀,左手拿旗,面对临清城数百步,口中念念有词,当炮弹快要距离他一两尺时就坠地,就在官兵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忽有一位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开内衣,以阴门面向四王爷,同时命官兵开始燃炮,遂见落地的弹丸忽跃而起,击中四王爷,此法被认为可破王伦军的妖术之后,官军遂令一些老弱妓女,裸身依凭在城墙上,并泼洒鸡血、粪汁,此后炮无不发,发无不中(表一,案例4)。[28]
此外,《六合内外琐言》一书亦提到:
妖人汪仑施药煽愚民,构祸齐州,凡十女弟子而两传,妖领之,凡五十人而一骡,渠乘之,破三县,围清渊城。……是时统军荆公,以天子命率王师解清渊之围。公善韬略,先斩一大将军,军中股栗,无或敢退避者,贼至薄城,公命以大炮击之,贼以女弟子厌炮咽其声,公大惊曰:『此阴门阵也,须破之。』令城中卒剃下体毛,置炮中,击死贼无算。贼又令小男子,年十五以上者,裸体执弩矢,射城中,多死伤,公曰:『贼猖獗以阳门来乎?』令以群娼列於城上,露其阴,老阴少阳,小男子败矣。[29]
此处的「妖人汪伦」指的就是上述的王伦,一句统军荆公的「此阴门阵也,须破之。」道出了阴门阵在当时战争中,已是一项常见的战术,阴门阵/反乱军及阳门阵/清军的对应方式并非绝对的,有时亦会出现相反的场面。清军在面对王伦之乱女弟子的阴门阵攻势时,采取剃士兵下体毛置於炮中的方式对付女弟子军的法术;王伦军则反命年十五岁以上的小男子,裸体手执弓弩射向城中。面对王伦军的反制,清军又叫年老妓女站於城墙上,暴露下体的「阴门阵」方式来厌胜敌军(表一,案例5)。
有关阴门阵的事例一直到清末都未曾中断,例如祡萼在《梵天庐丛录》中就记有他转录当时笔记中一条名为「婚人厌炮」的资料(表一,案例9):
光绪甲午春,四川顺庆土匪作乱,徐杏林时以全省营务处代理提督,适患卒疾,遣部将马总兵雄飞带兵平之,一日,战未毕,忽见对阵之匪拥出妇人数十,哭声震天,官军大炮竟不燃,此见诸近人笔记者,名曰婚人厌炮,昔读《六合内外琐言》,亦有妇人裸以厌敌之说,诚不值通人一笑,此种邪说,流传甚久,亦甚广,时至今日,尚有信者,可忧也。[30]
在这条资料中,柴萼亦提到了他曾在《六合内外琐言》中读过相关的记载,并认为这样的裸妇厌炮的法术流传甚久甚广,直到当时都还有信众。阴门阵可以厌炮的说法不仅流传於地方,甚至连中央权臣亦深信不已,例如清人高树在《珠岩山人三种》就提到一首诗,诗云:「八卦由来属太阴,肉屏风下阵云深,何时玄女传兵法,欲访青州张翰林」,这首诗后面有一小段注解说到,山东张翰林曾经告诉相国徐荫轩,东交民巷及西十库曾有洋人叫妇人裸体围绕,以御枪炮的例子,当时闻者皆匿笑,徐荫轩却对此深信。文后高树又以一诗「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装论坐经筵,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提到徐荫轩在宫中讲说阴门阵的胜况。高树的注解是,徐荫轩在公开场合讲程朱理学,并担任大阿哥的塾师;私下则对各翰林讲说阴门阵。高树最后还提到,他曾听豫瞎子说,有位樊教主曾割教民妇女阴部,排列阴门阵以御枪炮(表一,案例10)。[31]
厌炮之术到了中英鸦片战争时,成为清军对付英国船坚炮利的方法之一。当时清军认为英军从风波摇荡的海上进攻,还能将炮弹准确的击中清军,而清军却不能,其中必有善数术者在其中作法。清军将领遂令保甲收遍附近所有妇女便器作为厌胜的器具,载於木筏上,便器口向前,竹筏则排列在英军船舰前面(表一,案例6)。[32]目前有关太平天国时期的这部份料尚不多见,但根据日本学者铃木中正的太平天国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安徽颍上县,曾有官兵叫数十名刚满月的产妇,身穿红衣,手执符咒,站在城墙上,果然使得太平军的火炮顿然停止轰击(表一,案例8)。[33]
(三)阴门阵的厌胜特色
根据上述阴门阵的探讨,可综合出以下几点特色:
- 据目前所见资料,笔者推测阴门阵的明确阵法源始於明末流寇之乱 时。一方面是因为火炮普遍用於官军的讨伐战役中所造成的重大震撼及杀伤力;另一方面是当时乱事的根据地大多起於西南地区,此种厌胜阵法与少数民族的巫术及民间宗教特色不无关连。[34]
- 阴门阵可说是用於战事上的一种厌胜法术,当敌方使用此套阵法时,必须以相对应的数术阵法来反制,而非正统的兵家之术。阴门阵不仅可对付敌人之枪炮;亦可在当对方使用另一套咒术时,反制对方使其法术失效,例如义和团运动时。透过阴门阵,我们可发现官方所谓的「妖人」、「妖术」,其实就阵法性质来看,官/妖之间并未有多大的区别,想对地,所反映地只是官方对以宗教方式反抗国家权力的边缘势力的污名化。[35]
- 阴门阵的主体为裸露的女体,且特别强调「女阴」部份,凡与女性性器官有关的经血、经布及便溺秽水皆可当作厌胜之物。此外,一些法器(箕器)和动物(牛羊狗鸡的头)亦可加强阴门阵的厌胜功能。箕器在古代和「帚」一样,除了当一般日常生活中扫除污秽之物的器具,并具有在祭坛中担任拔除秽物的祭器用途。[36]此后,到了隋唐之后,随著「紫姑信仰」的流行,箕器在扶鸾仪式中所扮演的咒术角色更加明显。[37]
-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历来传统战役中,参与阴门阵的妇女大多以被胁迫性成份居多。文献中,参与者身分大多以「裸妇」称之,所以要做更细致的分析稍嫌困难;不过有些身分特殊者??孕妇及妓女会被特别强调;这或许是因为前者带有即将孕育生命的力量,这些被视为是有威胁性的;[38]至於妓女,一方面可能与她负面的社会形象有关,另一方面,妓女因从事性工作,身体的污秽可能被视为较一般妇女要高,从以阴克阳或污秽的角度来看,这或许带有较常人更具威胁性的厌胜力量。
- 反制阴门阵的方法亦琳琅满目:(1)动物血液或器官:如洒黑狗血、鸡血、羊角烟。对於「狗血」所具有的厌胜功能,明末医家李时珍(1518-1593)於《本草纲目》的解释是:「术家以犬为地厌,能禳辟一切邪魅妖术」。李时珍认为这样的观念早在先秦时就有,像秦德公杀狗砾四门以御灾的例子,[39]《风俗通义》则记有当时人杀白狗血题门以辟不祥的例子,[40]可见狗血具有驱邪功能的观念可上溯自先秦时代。民国初年汉学家J. J. M. de. Groot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中提到,狗血如同鸡血或鸭血一样,具有驱逐恶灵的功能。[41]当代人类学家Emily Ahern亦认为,当血液从被屠动物体中像经血一样流出时,会释放著蕴含善或恶的威力。[42]羊角烟的厌胜作用,《本草纲目》的解释是,在入山前烧羖羊的角,则可辟除恶鬼虎狼的侵袭。[43](2)人体排泄物:如便溺或悬挂便器。(3)男性性器官:如剃士兵下体毛,裸露十五岁以上男子或僧人阳具的「阳门阵」。[44]
表(一) 阴门阵厌胜火炮对应表
发生时间
对应方式
反制方式
补充
资料来源
1明末播州之乱
裸妇/火炮
狗血、
羊角烟/裸妇
《平播全书》
2崇祯九年(1636)
裸妇/火炮
便器/裸妇
《流寇志》
3崇祯十五年(1642)
裸妇/火炮
僧人/火炮
阳门阵
《守汴日记》
4乾隆三十九年(1744)
邪术/火炮
裸妇、妓女、鸡、狗血/邪术
官兵以裸妇助炮
《朱批奏折》
5乾隆三十九年(1744)
1.女弟子/火炮
3.少阳/官兵
2.男子体毛/女弟子
4.妓女/少阳
王伦之乱
《六合内外琐言》
6鸦片战争
邪术/火炮
便器/邪术
《夷氛闻记》
7太平天国
(1851-1864)
裸妇/火炮
《朝花夕拾》
8太平天国
产妇/火炮
产妇身著红衣
9光绪二十年
(1894)
哭妇/火炮
《梵天庐丛录》
10义和团运动
(1900)
裸妇/火炮
《珠岩山人三种》
四、结语:从私领域到公领域??女体禁忌范围的扩大
近来学者表示,女人与污秽(pollution)的关系在人类学界已累积相当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将焦点集中在月经的污染问题上,而Mary Douglas的象徵结构分析是最常被引用来讨论女性经血与生产污秽的理论架构。她将女人的污染物质类比於象徵的或社会秩序之异常,污染物质亦象徵代表著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具有危险的象徵。[81]历来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从田野的角度来探讨,像从早期的Ahern,到近来的施芳珑、翁玲玲、王明珂的研究,都多少受到Douglas的影响。[82]本文所处理的和上述人类学研究虽同是有关女体禁忌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从明清的女体与战争关系著手,透过文献分析,将焦点集中在女子裸身露阴的象徵意义上。若我们拿阴门阵现象和明清之前有关女体的禁忌作一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除了部分宗教仪式外,之前的禁忌大多属於於女性个人私密性的活动,举凡生产或月经期间的禁忌,其威胁范围较小;阴门阵的出现或可视为是女性禁忌的范围从私领域扩大至公领域,一方面是厌胜主体的范围扩大,像从月经的禁忌扩大至女性裸体的禁忌,另一方面是厌胜对象范围扩大,像以男性为主体的战争。
总的来说,阴门阵提供了探讨明清的女体与战争关系一个相当好的例子。我们认为,日本学者泽田瑞穗与相田洋昔日的「以阴克阳说」似乎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阴门阵现象。当我们将视野扩大至女体与厌胜关系时,义和团团民的心态反映了明清时妇女裸身具有污秽的象徵意义,而这套观念自明末以来被运用在战事上。义和团运动时,裸妇被视为是保护洋炮,破除法术的主角,这和明末清初抗炮阴门阵背后所隐含的污秽的象徵概念如出一辙,都认为女体??尤其是裸妇具有厌胜力量。义和团的这种视女体污秽的观念正可解释何以在明末以来的战争,会出现用裸妇来厌炮的阴门阵现象。明清女性透过阴门阵这种相当残忍的厌胜方式参与战争的例子,可谓是史无前例。可惜的是,除了鲁迅保姆以此表示自己的用处以外,所记载的全都是男性的污名化观点,女性对於这种事的看法究竟如何?就目前资料看来,可能永无答案。
(附图一)
出处: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17.
Women’s Body and Warfare: The Re-exploration of Yin-men-ch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u-shan Chiang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here are many groups of rebels who had used naked women to fend off firepower of government troops since the late Ming. This magic method—Yin-men-chen—was practiced up to the Taiping rebels and Boxers of the late Ch’ing. For example, The nurse, who took care of the famous writer Lu Xun, when he was a little boy, told him the following story about her own experience with the Taiping rebels: “When government troops of Ch’ing came to attack the city, the Long Hairs (the Taipings) would make us take off our trousers and stand on the city wall, presuming that the cannon could not be fired; if fired, it would burst!” The story is very interesting. There are many similar cas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is thesis will re-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men’s body and warfare through Yin-men-chen. Previously, some scholars had dissussed the topic, such as James Parson, Sawada Mizuho, Soda Hiroshi, Li Jianmin, and Paul A. Cohen. Based on their researches, this article will re-explore the topic in two aspects: women’s body and cannon, and women’s body and magic power. Topics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1)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Yin-men-chen? (2)Why can women’s naked body fend off firepower? (3)What kind of Women has the potentiality—power of resisting firepower? We suggest that naked women, above all, menstruating women, was a symbol of pollution, which would negate the power of cannon as well as black magic.
Key Words: women, body, warfare, Yin-men-chen, cannon, magic, women history, body history
*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班研究生
本文初稿曾在「第四届全国历史学论文讨论会」宣读(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3/28-29),二稿在「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上发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6/11-12),承蒙梁其姿师、李建民、康豹(Paul Katz)、张嘉凤、祝平一、李贞德、林富士、王道还、李孝悌、范雅清、周维强、清华历史所、与会学者、及匿名审查者等诸位师友的指正、建议与资料提供,谨此致谢。
[1] 鲁迅(1881-1936),《朝花夕拾》,收於《鲁迅文集》(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页222。Susan Naquin,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98. ;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编,《元明清国家「支配」民众像再检讨》(福冈: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1984),页192。
[2] R. H.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 C. till 1644 A. D. ( Leiden: E. J. Brill, 1961). 此处是引用中译本,见李零、郭晓惠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台北:桂冠出版社,1991),页241。
[3] 嵇童,〈压抑与安顺¾¾厌胜的传统〉《历史月刊》123:28-35 (1999.1)。
[4]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16-117.
[5] 有关阴门阵的介绍或研究,目前所见有以下五篇,James Parsons, “Attitudes towards the Late Ming Rebellions,” Oriens Extremus 6 (1959)。此文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提到阴门阵现象的论文。泽田瑞穗,《中国咒法》(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页402-404,此文举出了一些阴门阵的笔记资料,对於后学者相当有帮助。相田洋,《中国中世民众文化:咒术、规范、反乱》(福冈:中国书店,1994),页54。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8-134。李建民,〈「阴门阵」考——古代礼俗笔记之二〉,《大陆杂志》85.5 (1992)。
[6] 西方学界有关身体史的研究回顾,见Roy Porter, “History of the Bod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06-32。
[7]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92-95,「女子当兵和服劳役」。
[8] 王子今,《中国女子从军史》(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
[9] 《中国中世民众文化:咒术、规范、反乱》,页50。
[10] 《明史》,卷212〈列传一○○〉:5623。
[11] [明]李化龙(1554-1611),《平播全书》,收於《百部丛书集成》第94辑15、16函(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1966),卷5:31-32。
[12] 有关明末杨应龙之乱,见冈野昌子,〈明末播州杨应龙乱〉《东方学》41(1971)。
[13] 《中国女子从军史》,页224。
[14]《平播全书》,卷11:46,「破贼厌镇法」。
[15] 《平播全书》,卷12:82,「陈总兵」。
[16]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卷12:290,「厌法」。
[17] 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443。
[18] 《明史》,卷249〈列传一三七〉:6451-52。
[19] 《明史新编》,页443。
[20] [清]彭孙贻(1615-1573),《流寇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页36。另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立览堂丛书据述古堂抄本景印),卷9:1-2。
[21] [明]李光壂,《守汴日志》(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据崇祯十六年版(1643)点校),页7;另见《中国野史集成》29集(成都:巴蜀书社,1993),卷14:11,其内容为「崇祯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贼用阴门阵,城上以阳门阵破之……贼驱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骂,贼炮亦倒泄」。
[22] [清]郑廉,《豫变纪略》,收於《三怡堂丛书》(清光绪至民国间河南官书局刊本),卷4:1。《武编前集》中亦记有「兵士务去襦胯方胜」的数术阵法,页649。
[23] [清]董含,《三冈识略》(申报馆傲聚珍排印本),卷1:13,「阳阵阴阵」。有关「牝牡」的考证,见吴承仕,〈男女阴释名〉,《华国月刊》2.2 (1924):2125-26。
[24] [清]计六奇,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
[25]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收於《明清史料汇编》第4集4-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73),卷12:26a。
[26] [清]魏源,《圣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道光刻本影印,1997),「乾隆临清靖贼记」,卷8:373。
[27]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七日舒赫德奏摺」,转引自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1043-44。
[28] [清]俞蛟,《临清寇略》,收於《梦广杂著》,见《中国近代小说史料汇编》第22辑(台北:广文书局,出版时间不详),卷6:3。
[29] [清]屠笏岩,《六合内外琐言》,收於《中国近代小说史料汇编》第17辑(台北:广文书局据宣统三年版影印),页52。
[30] [清]柴萼,《梵天芦丛录》(台北:禹甸文化事业公司据中研院史语所藏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中华书局石印本影印,1976),卷30:21-22。有关团民攻打西十库教堂遭遇洋人以裸妇克之一事,本文在第三节有详论。
[31] [清]高树,《珠岩山人三种》,收於《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页9。
[32] [清]梁廷柟(1796-1861),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北京:中华书局据道光末年版点校,1959),页59。
[33] 铃木中正,《中国宗教革命》(东京:东京大学,1974),页261-62。
[34] 有关中国近代火炮的演变及发展,参见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页74-80。钟少异编,《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159-76。
[35] 有关历来政权对妖道与妖术批判的讨论,参见葛兆光,〈妖道与妖术——小说、历史与现实中的道教批判——〉,《中国文学报》57 (1998):1-26。
[36] 加地伸行、范月娇译,白川静著,《中国古代文化》(台北:文津出版社,1983)。
[37] 许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页8-28。
[38] Emily M. Aher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pp. 269-90.
[39] [明]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卷50:2716-18,「兽部」。
[40] [汉]应劭,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台北:汉京出版社,1983),页418。
[41] J. J. M. de Groot, The Religions System of China, Vol. 6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eiden: E. J. Brill, 1897), pp.1006-09.
[42] Emily M. Aher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Margery Wolf, ed.,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74.
[43] 《本草纲目》,卷50:2740,「兽部」。
[44] 相田洋,《中国中世民众文化:咒术、规范、反乱》,页54。另见泽田瑞穗,《中国咒法》,页402-04。泽田认为以女阴去对付火炮,有阴阳对应相克的观念,因此用带有阳刚象徵的十五岁以上男子及六根清净的僧人,正符合这种阴阳相克的关系。李建民亦认为以妇阴来对抗火炮,具有阴阳相克的意涵,参见李建民,〈「阴门阵」考¾¾古代礼俗笔记之二〉,页3。
[45] 泽田瑞穗,《中国咒法》,页402-04。相田洋,《中国中世民众文化:咒术、规范、反乱》,页54。
[46] 李建民虽然亦解释女性的性器官或排泄物有「伤害力」,但他所根据的资料是明末医家李时珍的看法,至於一般民间如何看待女性的身体,李建民并未进一步处理,见李建民,〈「阴门阵」考——古代礼俗笔记之二〉,页3。
[47] 〈「阴门阵」考——古代礼俗笔记之二〉,页2。
[48] 宫下三郎,〈禁忌与邪视〉,薮内清先生颂寿记念论文集出版委员会编《东洋科学技术:薮内清先生颂寿记念论文集》(京都:同朋舍,1982),页223-37。感谢李建民先生提供此文。
[49] 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与医疗照护〉(发表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二次讲论会,1998/9/21),页30。
[50]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pp. 128-34.
[51] 同上书,页28。研究义和团运动著称的Esherick (周锡瑞)曾提到「红灯照」的特色:「人们相信他们有极大的魔力,他们能在水上行走、空中飞行、喷火烧教民房子、在海上攻打敌舰和制止枪炮,这些都远超过义和团自己所夸跃的那些本事,这反映了女人尽管不洁,却有非凡的能量。」见Joseph W.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98。有关教堂内挂妇人皮的记载见[清]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收於《义和团》,页191-93。[清]艾声,《拳匪纪略》,收於《义和团》,页458。
[52] 有关十九世纪末,中国民众视西方教堂为陌生空间的排斥与恐惧,参见杨念群,〈论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发表於「中国十九世纪医学讨论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1998/5/22),页1-53。
[53] [清]袁昶,《乱中日记残稿》,收於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页348。
[54] 《拳匪纪略》,页450。
[55] 佚名,《天津一月记》,收於《义和团》,页151。
[56] [清]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收於《义和团》,页16。
[57] [清]柳溪子,《津西毖记》,收於《义和团》,页153。
[58] [清]仲芳氏,《庚子记事》,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78),页191。
[59] 同上,页17、28。
[60] 同上,页163。
[61] 陈青凤,〈义和团运动中的妇女组织——红灯照——的考察〉,《政治大学历史学报》9 (1990):143-62。
[62] [清]管鹤,《拳匪闻见录》,收於《义和团》,页474-76。
[63]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页13。
[64] 同上,页19。
[65] 《天津一月记》,页147。
[66] 《拳匪闻见录》,页470。
[67] 《天津一月记》,页142。
[68]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页9。
[69] 《天津一月记》,页148。
[70]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页12。
[71] 同上,页13。
[72] 《封神榜》(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页697。《济公传》亦有相当多这方面的记载,见Meir Shahar, Crazy Ji: Chinese Religion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9.
[73] 宫下三郎,〈红铅——明代的长生不老药〉,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编,《中国科技史探索》(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页561-71。
[74] 《菽园杂记》,页45。
[75] 《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卷52:2952-53,「人部」。
[76] [明] 褚人获(1635-?),《坚瓠广集》,页5756-57,「娼家厌术」。
[77] 《天津一月记》,页145。
[78] 江绍原,〈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晨报副镌》(1926/3/8,页17-18;1926/3/10,页21-22;1926/3/13,页29-30;1926/3/15,页34-35)。此文原被视为佚失已久,近来友人范雅清在研究周作人时,意外在《晨报副镌》中发现,在此感谢他的资料提供。有关江绍原的天癸研究由来,见其专书《血与天癸:关於它们的迷信言行》的导言,收入王文宝、江小蕙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页161-93。
[79] 参见Emily M. Aher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pp. 269-90.
[80] 此外,有关明清时期医学对妇女经血、身体与性别关系的论述,可见Charlotte Furth, “Blood, Body and Gender: 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1600-1850,” Chinese Science 7 (1986):43-66.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81] 林淑蓉,〈婚姻、家庭与性别:中国侗族的两性关系与性别象徵意义〉(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1999/5/28-30),页19。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1966).
[82] 施芳珑,〈姑娘仔「污秽」的信仰与其社会建构——以北台湾三间庙宇为例〉,发表於「妇女与宗教小型研讨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1996/6/8);翁玲玲,〈女人、不洁与神明——台湾社会经血信仰的传统与现代〉,发表於「妇女与宗教小型研讨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1997/5/9)。Sara Delamont, Knowledgeable Women: Structuralism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lit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19-24 ; 王明珂的「毒药猫故事」研究亦引用了Douglas的污秽与边界概念来说明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认同与对外界的疑虑与恐惧,见氏著,〈女人、不洁与村寨认同:岷江上游的毒药猫故事〉,发表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洁净的历史研讨会」(1998/6/11-12)